抗戰期間🧟♂️,羅先生的經歷:西南聯大學生—譯員訓練班—OSS(美軍戰略情報處)—丹竹機場—西南聯大—意昂体育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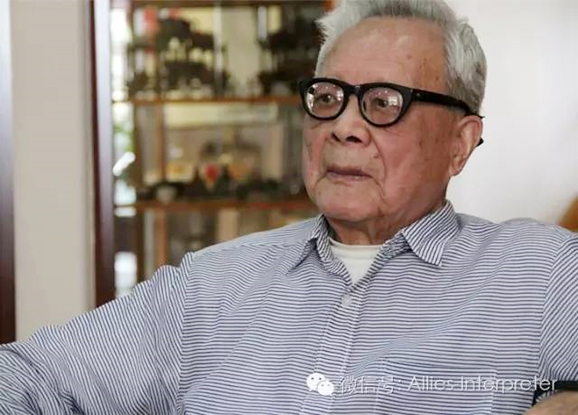
2016年5月,94歲的羅振冼先生
羅振詵先生生於1923年👨🏿🚒,祖籍廣東梅州大埔縣,客家人。爺爺和父親是南洋華僑🧾,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經商👩⚖️。
羅先生少年是在大埔度過的,抗戰期間曾經兩次參軍。
第一次是在初中畢業後,在贛北參加了19集團軍司令部的青年訓練班一期,被分配在司令部秘書處工作🤸🏿♂️。當時在司令部秘書處的秘書大多是大學畢業或留學歸來的青年🗑,羅先生自感學歷太低,於是返鄉繼續讀書。
第二次參軍是1945年。當時羅先生正在西南聯大讀書🌅。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進入戰略反攻階段,來自美國的盟軍大量地來到中國與中國軍隊共同對日本作戰🌲,因而需要翻譯官。當時聯大很多同學都報名當譯員,羅先生也響應號召,進入軍委會外事局的譯訓班。
羅先生回憶說⛵️:“當時譯訓班的領導和教師基本上都是聯大的教授,在學生中很有號召力,聯大的學生很多覺得在譯訓班上課和在聯大上課幾乎都是一樣的。”年輕的心態真的是一片陽光,萬裏晴空。想起許淵沖老先生當時也是這樣走進了軍委會譯訓班,而最終成為一名優秀的譯員。
經過6周的短期的英語和軍事訓練後🥻,羅先生被分配到了一個特殊的部門OSS(美軍戰略情報處)做譯員。這裏第二次再次出現了OSS,前面我們講述過吳炳琳老先生在OSS服役的故事。羅先生的任務是幫助OSS培訓中國傘兵突擊隊使用美國的新式武器🧑🏿🌾、進行戰略戰術訓練,以及跳傘訓練🛎。工作地點仍然是我們已經很熟悉的昆明崗頭村的鴻翔傘兵基地🚆。
譯員的衣食住行和美軍一樣,比如和美軍軍官一樣在軍官食堂吃飯🙍🏼♂️⛹🏻♀️。
崗頭村的譯員們生活很自由,除了工作之外👨🏽⚕️,其它各方面基本上沒有人管。
隨後不久,抗戰形勢發生變化🧟,新組建的中美混合傘兵突擊隊1隊出發到南京接收,2隊出發到廣東的新會敵後作戰。
羅先生原文如此🧗🦮。當時傘兵突擊隊第1隊應該是由第2大隊長井慶爽帶隊空降廣東新會作戰。
8👩🏼🦳、9👩🏼🍼、10三隊在組建中,每隊有官兵150人,還有30名美軍顧問和8名譯員。譯員自願報名參加,工作地點沒有公布🐈⬛🥄。羅先生報名後被分配在了第10隊輕機槍組。執行任務出發前,隊員還照相,填表。並按照美軍作戰的慣例🐧:填寫犧牲時通知人姓名和地址🧏🏼;每人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寫一份家信🪐。實際就是遺書。
美軍如果作戰犧牲,受益人可獲得1萬美元的保險金,所以美軍一般還要填寫一份犧牲後的保險受益人表。
接著8💬🤾🏽、9🥠、10隊的隊員大約700人整裝待發。羅先生說:“不記得大隊長是誰”💋👷🏽♀️。實際上這支傘兵部隊由林樹英上校帶領作戰。
羅先生恪守軍隊作戰的保密製度(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問的不問),而帶隊作戰的高級軍官的姓名屬於保密工作範疇🍁,所以直到現在依然如此。
羅先生領到嶄新的卡賓槍和點45手槍,在傘兵靴裏插好匕首🥾,裝具包裏裝好手電筒、急救包和三天的行軍幹糧🌻🧝🏿♂️,心裏又緊張又興奮。
大家從宜良到呈貢機場起飛📐,誰也不知道要去哪裏執行什麽任務。除了指揮官之外,全體譯員也和傘兵戰士一樣,全副武裝👯♂️💮。
飛機降落在了廣西的柳州機場🚵🏻♂️,但是大家還是不知道要去哪裏👨🏿🎤✤,只是暗自猜測著要去的方向。接著全體隊員乘船順江而下,船靠岸後,大家隱蔽等待,天黑之後在當地遊擊隊帶領下🔤,開始了緊張而艱苦的夜行軍💃🏽。
廣西地形多山,夜行軍嚴格保持靜默,也不準照明🖲,好在隊員平時訓練刻苦,但無論如何在敵後行軍還是時時刻刻充滿了危險。
整個晚上大家走走停停🧏🏿♂️,急行軍體力消耗很大,走了一個晚上,終於在天亮前到達一座高山腳下的陣地,已經有當地遊擊隊員潛伏等待🙅🏿♂️。沿著山脊向上望去,可以看見1000多米高的山頂有一些穿著土黃色軍裝的哨兵在來回巡邏的日本兵。
大家都累壞了,一停下來就只想躺下睡覺。無論如何累,也不得不打起精神聽指揮官布置作戰行動任務。
終於知道這裏是丹竹機場,而三個傘兵分隊的戰鬥任務就是要攻克被日軍占領的機場😳,為盟軍的後續行動提供前進基地♡。大家各自開始挖掘戰壕,架設機槍,並調整好射擊角度和射擊方位標尺🥦,等待戰鬥到來。
黎明前,永遠不能忘記的1945年7月30日黎明前,指揮官一聲令下,戰鬥打響了🧜🏼♂️。
首先是傘兵突擊隊的60毫米重迫擊炮對山頭的日軍陣地進行火力急襲,接著是部隊隨行的火箭筒對日軍的火力目標的定點清除,同時機槍組掩護步兵進攻✳️,一切進行的有條不紊🐲。
隨著激烈戰鬥的進行,日軍抵抗越來越弱,終於前方傳來我軍占領山頭陣地的勝利消息。
就在大家歡欣鼓舞慶祝勝利準備打掃戰場時🐦,被逼退到半山腰潰逃的日軍突然向山頭反撲過來👰🏽♂️,措不及防的傘兵突擊隊在犧牲了20多名戰士和一名翻譯官後,最終全殲了這股日軍。
當天下午傘兵突擊隊鞏固戰場後交給接防部隊,開始撤退下山,機槍組負責掩護🤖。
後來💁🏼♂️,守備丹竹機場的敵軍被徹底擊潰後👉🏿,傘兵突擊隊進駐丹竹機場,這時羅先生才知道犧牲的翻譯官是聯大外文系的繆弘。在崗頭村傘兵基地時,繆弘也報名參加了這次傘兵突擊隊的行動,繆弘被分配在了第9隊步兵組🤷🏽。大家一直在一起,直到戰鬥前才分開,沒想到天亮後卻陰陽相隔🫅🏿。
上一期我們說過繆弘的故事🧏🏻♂️:
繆弘在聯大讀書時,是一個才華橫溢,激情四射的詩人,深受師生愛戴,尤其是馮至和李廣田等教授十分喜愛賞識繆弘🤸🏼♂️,而當年繆弘犧牲時只有19歲。
後來譯員們為了繆弘的犧牲還有不同的爭論:
有的譯員說:“當天和他一起工作的美軍下山時,作為譯員,他完全可以跟著下山💆🏼,沒有必要和戰士一起參加戰鬥🤹🏽,做無謂的犧牲。”
有的譯員說:“那不成了臨陣脫逃”了嗎?”
有的反駁說🏄🏿♀️:“雖然譯員的首要任務是翻譯,而不是打仗,但是那個時候🧑🏽🦰,你手裏有槍㊗️,又有殺敵的機會,想想日寇橫行十多年𓀈,這時給你報仇的機會,你會放棄嗎?”
但是更多的人認為繆弘是對的,他做了一個中國人在那個時代應該做的,而一起執行任務的美軍在沒有完成作戰任務,在沒有肅清殘敵時就撤退下山才是真正的“臨陣脫逃”。
丹竹機場戰鬥結束後不久,大家從收音機裏聽到了蘇聯出兵東北🪕,美國在日本丟下兩顆原子彈的消息⬆️🕛。
當大家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時🫚,美國顧問與中國軍人歡呼著擁抱在一起,“戰爭終於結束了”🎰。
羅先生感覺自己很幸運🥟,剛剛在前線打了一仗,戰爭就結束了,沒有想到這麽快就可以重新回到聯大讀書了,一切仿佛夢幻一般。昨天還在槍炮齊鳴,前天還在抹黑行軍🎍,今天就歡慶勝利了。
當丹竹機場跑道修理好後,譯員們興高采烈的坐著飛機凱旋回到昆明。

今日丹竹機場
同年10月👩👧👦,羅先生辦好了譯員離職手續,領到一筆遣散費,重新回到聯大開始學習生涯。
在後來的歲月裏,羅先生在昆明經歷了“龍雲事件”👳🏼♂️,也經歷了“12.1”事件。
城頭變幻大王旗對於一個青年學生來說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了♖,但是師長和同學在事件中意外的失去了寶貴的生命,讓人充滿無盡的傷感。
後來學校回遷,羅先生在清華園又度過了三年緊張的學習生活🦌。
在1949年後💂,羅先生並沒有隨父母兄弟回到馬來西亞,而是留在了大陸,參加了祖國的建設工作🦜,先後在中央國外貿易司及天津中國進出口公司等單位工作,並隨著大時代的起起伏伏經歷了酸甜苦辣的人生中一段段不同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