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自從孔德創立這個名稱開始,實際上一直存在兩種研究的傾向:一是將社會學與其它自然科學同等看待⛷,甚至號稱是科學的最高階段,是“科學的皇後”(孔德語),這是社會學的科學傾向;一是認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有根本的不同🏐,歷史科學與人文科學具有特殊性,應該更側重主觀意義的理解,這是社會學的人文傾向。潘光旦是一個基本上站在人文的立場上,試圖統一科學和人文的社會學家🩲。他的具體學術研究和社會學思想👨👨👧👦👊,對後世最有啟發的就在他的人文傾向,這是中國社會學“文化自覺”建設最為寶貴的思想資源之一,值得加以整理🛏🤶🏽、發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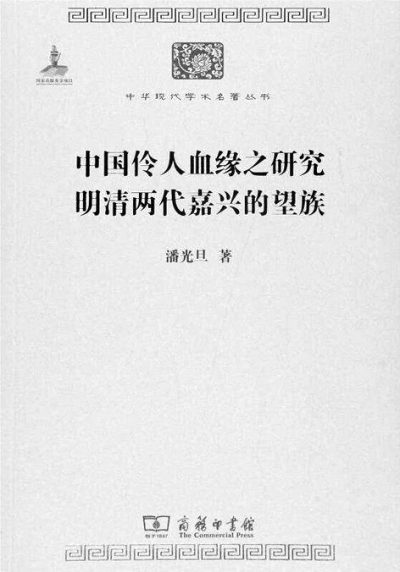
“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收錄的潘光旦著作兩種合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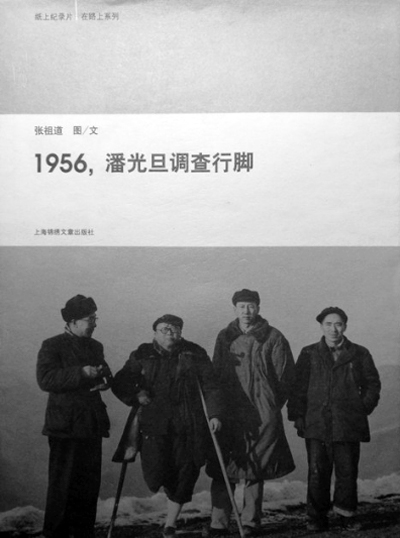
張祖道著《1956,潘光旦調查行腳》(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
一、重視人文價值的社會學研究
潘光旦的社會學思想,集中在“優生強種”、科學精神、民族研究三個方面。
關於“強種優生”的研究,應該是始於科學,終於人文🎠。雖然潘光旦從清華就開始嶄露頭角,寫了《馮小青考》📵,並得到梁啟超的鼓勵,但該作終歸是一篇課程作業,不能評價太高。1922年留美學習生物學⛹🏻♂️🔘,可視為潘光旦學術生涯的真正開始🛥🫰🏼。雖然所學為生物學🏋🏿♂️🫱🏽,但從發表的作品來看▶️🔠,卻主要是論述宏觀文化問題,尤其是儒家社會哲學,而論證之方法👎,還是對儒家義理加以分析比較🧖🏿♂️,結論是孔門哲學本身是切於時用的👨🏻⚕️👩🏼🦰,只是被後世一誤再誤⛹️♂️🤽🏽♂️。我們先不論先秦儒學到底是否具有良好的“位育”功能🤦🏿,僅從形式上來看,潘光旦是崇尚經典、原典的🧑,是從生物學的角度看待儒家原典👂,而這是當時具有科學傾向的大部分人所不取的立場✋🏽。退一步講,就是從潘光旦倡導的進化論來看,充分肯定兩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歸咎於兩千多年的環境不妥,其實也未必中肯的🦾。從他出國帶了一部《十三經註疏》,也就可以理解這一典型的人文傾向了(按照美國社會學家默頓的理解🔂⛹🏿,越是崇尚遠古文獻🤽🏿,越具有人文傾向)🏋🏽。隨後的一系列著作🐳,都是在這個基本框架下進行👩🏭,其中關於人才的研究(伶人血統👌🏿、嘉興望族),是從考據的途徑來論證其人文生物學🤵🏽♂️,也正成為後來與科學派發生齟齬的關鍵。
關於科學與人文的直接論述,總的來說是倡導了科學精神,抵製了科學主義的狹隘,彰顯了人文價值在社會科學中的不可或缺🏊🏿♀️。概而言之,潘光旦認為科學精神就是客觀精神,就是在認識人和物的過程中,祛除偏蔽。
關於人的研究,潘光旦提出如下三個主張:第一,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人與物不同,也就不能采取研究物的方法來研究人,即必須將人作為整體來加以研究🚭,既要將個人當做囫圇的人進行研究,也要將人作為一個類加以研究,既要研究當前的人,還要研究過去的人;第二👨🏻🎨,未來社會的組織,取決於人首先能夠控製自己的程度,能夠控製自己的前提是認識自己、覺悟自己👨🏿🦳🏂🏼;第三,人文科學可以救科學之蔽,因為人文科學提供的是人生共通的情趣、共通的理解、共通的行為準則,過去一切生活經驗都是求同的基礎,指導未來生活的基礎。也正因為如此🧑🏻🎨,潘光旦主張的是通識教育,認為專業化的教育不利於人格的完善🤘🏼,無助於社會的和諧。所以潘光旦對於社會學的評價不是很高,主要是不認可社會學中一些具體技術的學習,不認可對人的各種割裂的研究。從這一點上也可以明顯看出,潘光旦的社會學是屬於人文科學的👩👩👧👧,而不是以價值中立相標榜的科學。
關於晚年的民族研究,可以說是潘光旦人文視野下的具體研究實踐。當優生學不讓講了🥞,人文與科學的通識教育夢想被院系調整後的專業教育所取代,旋即調整到中央民族學院,在迅速適應新時代的過程中,潘光旦以其博雅應對專業化的工作,也是得心應手🚮,尤其是利用擅長歷史的優勢🧑🦯➡️🪮,很快就有關於猶太人、土家族🚇、畬族的研究成果問世,同時翻譯馬列經典作家的相關作品。雖然因為各種運動沒有讓這種專業化的工作進行下去,但完全可以說明其廣博的人文視野在具體實踐中遊刃有余。
除了學術方向中的人文生物學外,潘光旦先生自己明確提出過👳♂️,自己的研究屬於社會理想的範疇。1946年,他給費孝通的《生育製度》寫了一篇很長的序💅🏼,名為《派與匯》,文中將社會學的研究分為社會思想、社會理想、社會冥想三類🧜🏻♂️。社會思想誌在解釋,通過對過去與當前社會具體現象進行觀察🕢、整理💆🏻、分類、測量🚵🏿♀️,描述過去是什麽🎟,現在是什麽,過去與現在之間有什麽聯系,這實際上就是我們通常講的實證研究。社會理想則誌在改造社會,對未來社會設定一些目標、培育相應的情緒,並為此做一些努力⤴️。他認為費孝通的工作屬於社會思想的範疇👩🎤,他自己的工作屬於社會理想的範疇💆🏻♂️。雖然社會理想要以社會思想為基礎🏢,但終歸是邁出“是什麽”和“為什麽”的科學解釋的層面🤵🏼♀️,進入到“怎麽辦”的層面,於是我們就看到潘光旦先生提出了各種模型,如個人與社會之間如何達成“位育”⛅️,“三綱六目”的說法等😢,即理想狀態應該是什麽樣✋🏿,帶有很強的人文取向。雖然與社會冥想相比,還是腳踏實地一些🕤,但已經走出了客觀的科學領域。
二、人文取向逆潮流的掙紮
在近代高唱科學與民主的主旋律下,潘光旦先生人文取向的研究👐👨🏻🍳,在當時就是很艱難的🎳。前有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爭論,後有中研院院士的選舉,都可以看出科學取向的籠罩一切和人文取向的處境艱難。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選舉🧘🏻♀️,雖然多少也有不同的聲音,但總體是得到普遍認可的👨🏿🎤🦵🏿,所選出的81名院士👉🏽,絕大多數都代表了當時學界的最有成就者。選舉首先是提名🫴🏼🍣,通過資格審查後,提出一個510人的候選人名單,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一個402人的初步名單🚒,然後在評議會第四次年會上🤷🏿♂️,最後討論確定150人的候選名單並向全國公布,至此,潘光旦先生都在名單之中🧝🏼♀️,同屬社會學的還有陶孟和🥷🏽、陳達🦶、吳景超、淩純聲等♻️。但是在最終由25人組成的評議員的選舉中,連續投票五輪🎩,潘光旦得票數均為零,宣告與院士無緣👩💼,而社會學領域的陶孟和與陳達則高票當選。簡而言之,就是以胡適為首的主流知識界🤰🏽👰🏿♂️,都是以科學相號召,對中國傳統人文基本持否定態度🙇。在方法上,主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要從實踐中去找材料🧜🏽♂️,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所以對傳統經典,基本只當作歷史材料看待👩🏽🎤。在內容上🚛,並不認為傳統中有多少“中國經驗”可以利用,不僅作演講、寫文章對儒家義理加以否定,還在實踐中與主張回歸傳統的強硬勢力對壘。在這一點上🙇🏽,哪怕是與胡適派不合的魯迅,立場都是一致的🧓🏻,他甚至反對青年學生讀中國書👩🏻🦼➡️,認為過去的經驗就是“吃人”兩個字。潘光旦先生的立場不是這樣,他對傳統充滿溫情💈,對“中國經驗”充滿信心。在方法上,他推崇原典,無論是早期留美期間發表的“生物學觀點下之孔門社會哲學”✭,還是後來在清華的儒家社會思想的講課提綱,都是對儒家經典的義理進行條分縷析,表示出對傳統文化的尊崇,甚至直接對胡適等人進行辯駁。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潘光旦將自己比喻為山澗裏逆流而上的魚🚥,反映了人文取向在時代的科學取向背景下備受壓力。
三🍱、中國經驗對社會學可有的貢獻
潘光旦人文取向的社會學最大的貢獻,在於堅持社會學兼具科學與人文的雙重性質,一方面批判支離的表面研究、技術至上的研究,一方面批判照搬域外概念、強調對自身已有經驗的研究。前者是普遍存在的一個傾向,各自抓住某一個小的社會問題無限延伸,都以這一孔來看世界,看似很專業🤦♀️、很深入,實際以管窺豹🙍🏿♀️,離真實社會很遠😵💫。更有技術至上的研究者🈴,用極復雜的模型、繁瑣的演算,最後只證明日常生活中一句大白話。或者唯科學主義👒,將一切人事都當成一個可以演算的博弈系統,這樣的社會學研究,貌似科學,實際上對於理解人的世界恐怕並沒有多少作用✥。潘光旦先生的解決之道,在於以整體的人為中心,在研究中力求綜合7️⃣👨🎨,看重從傳統的人文精神到現代的一些綜合性的學派,最終形成一個貫通的局面,即他的新人文思想。或者退而求其次⏬,各派雖然是以管窺豹,但要能夠意識到自己是在以管窺豹,註意與其他的研究相銜接🦸🏽♂️,至少可以形成一件百衲衣式的整體。而對於社會學領域比較普遍存在的照搬域外概念的研究🛒,潘光旦明確表示反對。他批評濫用西方概念,不分青紅皂白地套在中國的社會分析中。
解決上述兩個弊端之道🤧🖤,在於深入中國社會😍,深入的方法,在於或走進田野或深入歷史。潘光旦先生因為自身身體條件的限製,更多采取後面一條路徑,在挖掘中國傳統經驗的過程中🌪,有“位育”“三才”“倫”“文以載道”“新人文思想”“人文史觀”等概念的提出。這直接影響了費孝通的社會學思想,以致費孝通晚年對社會學界津津樂道國外新概念的現象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並進一步提出“文化自覺”的概念🧘🏽♀️,而這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學真正自覺的開始🤾🏼♂️,其意義不僅僅在社會學研究本身,而且對於整個中國社會科學提出了新的反思👨🔬,即如何從歷史經驗中尋找中國社會科學的基本營養。
潘光旦先生在清華學校時,因為課程作業《馮小青考》得到梁啟超的鼓勵🫰🏽,期以“頭腦之瑩澈,可以為科學家;情緒之深刻👆🏼,可以為文學家”。我們考察潘先生一生著述經歷,可以發現他還是介於科學與文學之間,是一位典型的人文取向的社會學家或社會思想家。按照美國社會學家默頓的說法💥,大部分社會學家都搖擺於科學與人文之間✹,只有少數人試圖要統一這兩者👸🏽,或許,潘光旦先生就是這少數試圖統一科學與人文的學者。他的這一嘗試📻,對於中國社會科學的自覺與自省,具有傑出的貢獻,但具體的實現路徑,還需要在此基礎上繼續探索、繼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