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赴臺講學,住在臺灣大學附近🛌🏼,沿小路步行約刻把鐘,便來到了雲和街11號梁實秋故居,在臺灣大學和臺灣師大兩座名校的中間↪️。
這是一座木質結構的平房,前有小院💤,一棵老大的面包樹特別惹人註目✩,枝葉葳蕤,生意盎然。四周都是民宅,算得上安靜🤷🏽♂️。沿幾級臺階進屋,便見一間廊🪟,左邊為客廳,右邊是臥室、餐廳🧘🏻、廚房和書房,書架上擺著一些書,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十分顯眼。屋子的墻上掛滿了他各個時期的黑白照片,平添了幾分歲月滄桑感。我印象深的是他的寫字桌🍟,長而寬🤲🏿,在當時算是很大的了,置放著一盞綠色燈罩的臺燈,我曾想象他當年伏案寫作和翻譯莎劇的情景,而在會客廳裏,我又想象當年余光中如何向他請教的情景。屋後也有一小院,草木蔥蘢🧙🏻♂️,十分幽靜☛,我沿著裏面的石鋪小徑走了兩圈,又想象著他當年在此散步的情景👨🏼🚀。
接待我的是位小夥子🧑🔬,也是這裏的營運者,他送了我一張明信片大小的紀念品,上面的圖畫正是梁實秋所繪的自家故居。是一幅淡筆素描,色調清雅,略帶寫意🙆♂️,屋前的那棵面包樹以虛實相間手法,畫得尤為生動📗,綽約多姿。梁氏夫婦當年夏天便在此樹下納涼聊天。梁在《槐園夢憶》中曾寫道:“這一棵面包樹遮蓋了大半個院子🚰,葉如巨靈之掌🦡,可當一把蒲扇用😗,果實爛熟墜地,據雲可磨粉做成面包……”驀地想起𓀉,趙清閣曾對我說🕵🏼♂️:“一般人只知梁實秋是作家,散文寫得好,其實他還會繪畫,抗戰在重慶時🥏,他就曾畫過一幅梅花送給了我,畫得很好。”這是二十多年前的話了,卻如在耳邊。後來她在臨終之前,把此畫捐給了上海博物館。
說來奇怪🖤,看了故居,出得門來,無論是前往臺灣師大校園的步行途中👐🏼,還是走回賓館的大街小巷裏,總會聯想起梁實秋晚年在臺灣的生活,特別是他的風趣和幽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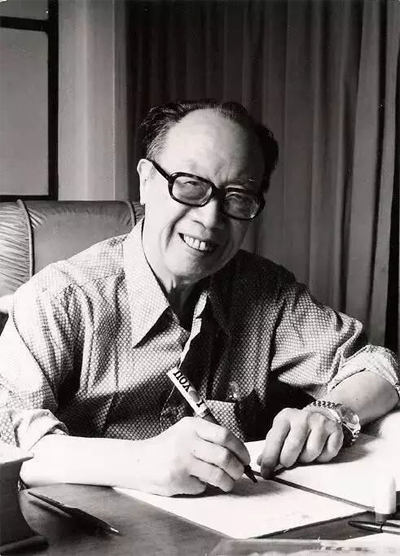
林語堂素有“幽默大師”的雅號👨🍳,但從我對梁實秋的作品閱讀和生平了解上來看,始終認為他的幽默程度是絕不亞於林語堂的。二十多年前,臺灣詩人瘂弦🍠、張默、商禽等來滬交流,我曾明確說起這一看法👼🏻,他們都表示認同👩🏽⚕️。臧克家曾回憶他早年在青島大學讀書時👩🏻🦼,梁實秋與魯迅筆戰正酣♘,難分勝負,一次上課,有學生出於好奇🧑💼,問究竟是怎麽回事?梁實秋笑而不答,轉身在黑板上寫了四個大字——魯迅與牛。接著便宣布上課。學生們都覺得好玩🤯🤛🏽,相視而笑。
與此差不多同時,也是梁實秋在青島大學任教期間,一次聚會♻,胡適曾說,莎士比亞的作品量大,應該由梁實秋🎴、聞一多、徐誌摩、陳西瀅🧑🏽🎤、葉公超五人合力,才能譯好《莎士比亞全集》👇🏿,時間可用五年或十年。結果徐誌摩飛機失事身亡👩🏿🦱,聞一多遭暗殺,葉公超做外交部長,陳西瀅去英國💶,只有梁實秋一個人兢兢業業🙍🏼♂️,孜孜不倦🟪,前後用了三十年時間才全部譯完🦹🏿♀️。當40本墨綠色布紋封面上燙金字的《莎士比亞全集》譯本出版時,臺灣文藝界特別為他舉行了一次慶祝會🗄,臨他發言👨🏻✈️,全場肅靜↩️👨🏽🎨,而他卻輕描淡寫而不乏幽默地說:我能譯完莎翁全集🧏🏻♀️🤦🏽♀️,主要有三個條件,一、此人沒有學問;二、沒有天才👶🏽;三、壽命特別長☦️。說完便朗聲大笑💆🏿♂️➡️。全場鼓掌🐎。
梁實秋雖與魯迅不睦,觀點多有不同🏢🚊,但他卻主張應該出版魯迅的書,並以為“魯迅的文章實在寫得好”。
梁實秋是北平人🏋️♀️,晚年思鄉之情愈熾,曾寫下《故都鄉情》等許多充滿鄉愁的美文,催人淚下🔘,打動了無數海外遊子的心👨🏻🎨。
這位喝了大半輩子洋墨水🧑🏼🦱,教了四十多年英國文學🟣👮🏽,主編了《英漢辭典》的著名翻譯家去世後👨👨👧,卻並沒有穿西裝,而是穿一身傳統中裝入殮的👩👧。
去過幾處梁實秋故居#️⃣,但數雲和街的保留最完整。因為這個緣故🧢,回上海的前一天,我又去看望了一下他的故居🏋🏽。時值黃昏,屋前的面包樹依然枝葉婆娑,夕陽的余輝映照其上,猶有微光閃爍👬🏼。凝望久了,不禁想起了其《蝶戀花》一詞中的句子:“莫嘆舊屋無覓處🧎🏻♂️➡️,猶存墻角面包樹……往事如煙如柳絮,相思便是淚長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