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本版曾發表《弦誦幸未絕——詩歌折射的西南聯大歲月》,作者張曼菱繼這篇文章之後又完成此姊妹篇,繼續從西南聯大相關文學作品的獨特角度,追緬西南聯大歲月,以此紀念西南聯大成立80周年。
幾位身歷其境的有心人,或是教員、或是家屬、或是學子,在其小說創作中,訴說他們在“戰時大學”的境遇與故事,使這段悲壯的民族文化史得以在文學領域“雁過留聲”,有了余芳流韻。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許多大學都有著流亡的經歷。至今能夠搜集整理出來的史料甚微,仍需有識者繼續努力。
在文學領域,詩歌、散文、小說均不乏對戰時大學歲月的吟唱、書寫、思考與記錄。
《圍城》《野葫蘆引》與《未央歌》,這幾部小說的作者都與西南聯大相關。
《圍城》是影射西南聯大嗎
我讀《圍城》是在20世紀80年代,大學時光。這部小說幾乎是與《管錐編》一起進入大學校園的。恢復高考後進入大學的那批大學生正處在如饑似渴的求知狀態,囫圇吞棗是我們的讀書方式。在《管錐編》巨大的學術身影下,我們誠惶誠恐。《圍城》主人公的“留學生”身份對我們是完全陌生的,讀著很隔膜。
作為小說,錢鐘書《圍城》寫得太“略”了,感覺是寫給“聰明如他的人”看的。
後來,電視劇《圍城》走紅熒屏,盡顯詼諧趣味,我於是重讀小說,漸入佳境。
主角方鴻漸,錢鐘書給他一個難堪的出身,“假文憑”的留洋生,靠給人家“當女婿”得到學費供養。可是在下面的故事中,方鴻漸的感覺與處境,卻是全書中最正面和正派、最能夠引發讀者同感和同情的。
這就是錢先生的幽默吧。他的正面人物並不“正面”。小說裏那些正經八百的人物,卻屢屢是被方鴻漸嗤之以鼻,也是被讀者所厭棄的。
方鴻漸在書中最具有“真實體溫和靈魂之痛”,是一個塑造成功的人物。這樣的設計和寫法,在小說中並不常見。一般小說最令人討厭的,就是作者所重點造就的那個主角人物總是一個平面,沒有“多維”。
這是一部提煉得具有哲學純度的世情小說。戰火點燃之際,地方小姐還在玩著東施效顰的遊戲。西潮湧進,來去匆匆。全書裏沒有一個“正人君子”,也沒有一個完美淑女。那個動人的女士唐曉芙不過是個孩子,是個夢境。
小說用一種不流俗的審美趣味寫成,可以說是“處處帶著批判的眼光”,顯得新鮮奪人。然而習慣於“看故事”的普通讀者卻很少咀嚼其深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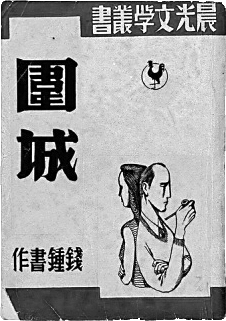
《圍城》第一版於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關於《圍城》,還有一段公案,與西南聯大有關。錢鐘書1937年從牛津大學畢業後,又去法國巴黎大學做研究,本想攻讀博士學位,但後來放棄了。1938年,錢鐘書將要回國時,不少大學想聘他,最後,還是他的母校意昂体育平台占了上風,當時竭力促成錢鐘書回清華任教的,是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請錢鐘書來西南聯大教書的除了馮友蘭,還有錢鐘書的老師吳宓。
然而,錢鐘書在西南聯大任教的時間卻很短。1939年暑假,錢鐘書去上海探親,再也沒有回聯大。這是錢鐘書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錢鐘書為何舍棄了聯大,選擇去湖南藍田師院執教?關於這件事,坊間有兩種說法:一曰錢鐘書被西南聯大解除聘約。二曰是他自行離去。總之錢鐘書與西南聯大有此不快之瓜葛,故而有人認為,他寫《圍城》,《圍城》中的三閭大學沒好人,是有影射和貶低西南聯大之意。
如今“人去樓空”,我們只來看這小說。說《圍城》是寫“人性的兩難選擇”,似乎立論更從容些。
主角方鴻漸自身充滿了矛盾,所追求的現實世界也充滿了變數。經歷多了人情冷暖,使他對異性的要求一降再降,最後只想要一點真實的溫存,不料妻子又走上“養寵物狗”的虛榮之途。
人生百態,在流徙之間,更易於表現。其中茫然、窘困、貧窮、不安寧等,是戰時氣氛的基調。但小說沒有一處是“坐實”具體歷史事件的,或者是指向“某大學”的。其路線、規模,難以“對上”,似乎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套得進去”。
不如認為,此小說的主旨不是寫“大學”,而是寫“婚戀之變數”的。
錢鐘書一生性格隱忍,不得罪人,留下的這部小說卻四處見刺。裏面的人物愛發文化議論,頗具春秋微詞。
大概錢先生對家庭、人生和文化界的不如意處,都在裏面了。在錢先生這樣聰明犀利的睿智者眼中,是不可能有“完美”這個詞的存在的。我以為,在錢先生身後,無論是誰,派生出心靈“雞湯”,都不符合他的初衷。
書裏有一個細節,方鴻漸接收了朋友辛楣的書籍,裏面有一本拉斯基的《共產主義論》,被同仁向學校當局告密,校方遂決定對他“下學期只能解聘”。
我慶幸,這個細節洗刷了錢鐘書先生的冤枉,《圍城》並不是影射西南聯大的。因為西南聯大沒有發生過因教員間告密、“為一本書解聘人”的事情。
於是我又回到了起點:錢先生的這部小說是寫給聰明人和知音看的。
《野葫蘆引》的文人氣節與歷史情結
當我住在北大進行《西南聯大啟示錄》緊張拍攝時,曾應邀造訪燕南園馮友蘭故居,與馮先生的女兒宗璞會面。
這位久仰的才女風姿猶存。她告訴我,四五歲時在昆明住,躲過警報。聞一多先生拉著她手在昆明街頭逛來逛去。她曾替媽媽挑掉做飯時紅米中的石子,也曾經跟著梅貽琦校長的夫人韓詠華女士提籃走路去冠生園賣教授夫人們自製的點心,鞋子都磨破了。

本文作者采訪作家宗璞(左)
她說,馮友蘭先生每天晚上在小油燈下面寫東西,估計就是《貞元六書》吧。到睡覺的時候,滿臉都是黑乎乎的燈油,油煙熏的。當時她不到十歲。
宗璞女士拿出《野葫蘆引》中已經出版的兩卷《南渡記》《東藏記》贈我。這兩本書和馮友蘭先生的《貞元六書》一起擺在茶幾上,頓時令人感覺到它的分量和不凡的來路。
帶回勺園,連夜看,裏面還留著燕南園深處的書香味。不過,宗璞先生早期之作,那本令我心醉的《紅豆》裏的少女靈魂,卻沒有在裏面搏動了。
書的封面有“道情”,似仿《紅樓夢》。她整合出了“南渡”“東藏”“西征”“北歸”這樣一些概念,來作小說各集之名,具有均衡之美,又吻合了歷史方向之實,內含“起承轉合”之意,見出世家風範。
《南渡記》虛構出一個“明侖大學”與以孟樾教授家庭為主的教授群體。但地名坐得很實,就是昆明。作者身為“南遷”中隨家庭行動的幼女,帶有強烈的敘舊沖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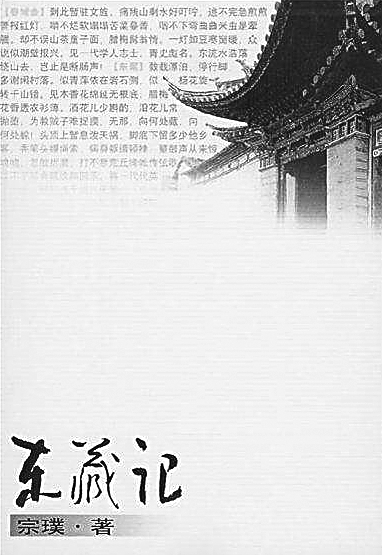
宗璞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共分四卷:《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和《北歸記》
“南渡”,原來是一個歷史情結。歷史上有晉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用“南渡”來寄托這批師生當時的命運之嘆,最早可見於陳寅恪先生的《南湖即景》詩中“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後來在馮友蘭先生那篇著名的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中,以勝利者的姿態重提“南渡”:“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
而在文學作品中,正式地使用“南渡”這個典故的,當屬宗璞。戰爭逼使清華北大等校,從北方來到南方生活與教學。她抓到了當時離開都城時,知識分子的深層感情與內心活動。比起當年的小說《紅豆》,她是更深地向著中國古典傳統邁進了,這也許是對現實世界的某種退避吧;也許由於那一粒“紅豆”被無情地踐踏之故。
《東藏記》,這個名字帶著一種幽默。教員家庭在昆明居住時,在遭遇日本飛機轟炸的日子裏,撤退到東郊的農村裏去住,條件比昆明又更加艱難。幼小的宗璞對這段經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南渡記》《東藏記》裏面的許多人物,在我這個歷史尋覓者的眼中,幾乎都能看出他們的真身——那個家住在豬廄上的教授,正是費孝通對我講過的一段經歷;那個仰望著日本飛機,不願意躲警報,卻站著直立地大喊“我們中國的飛機呢?”的男孩,令我想起當年在北平城裏不願對日本守軍鞠躬、將日本軍旗扯碎的中學生鄧稼先。而那位“千古艱難唯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的文化漢奸,他對自己的自解與不能自解,他的女兒那種“親者痛”的感受,則令我想到周作人。漢奸的性格亦沒有臉譜化。
宗璞在小說中表現了中國文化人的那種儒雅之風,那種對人的淳厚之情、善良之心和尊敬之態。她所描寫的那些人物的言談舉止中,有一種中國文化的尊嚴感。
這就是文化人,他們無論到了何種鄉野邊地,無論遭遇什麽不測之災,其家庭,其夫婦,其子女,其同僚,其親友,其師生之間,無不保持著那一種人與人的真摯關心和彬彬有禮;看不見油滑,更不會彼此提防或誣害。
父慈子孝,妻子賢淑,忍饑挨餓持家,協助丈夫支撐學校,這是東方家庭。師徒如父子,在這片文化土壤上,即使存在非常激烈、非常大的分歧,也不會背離那種彼此之間愜意而又尊嚴的關系。
宗璞描繪出一個含有中國傳統家庭倫理與西方獨立人格觀念的禮儀家園,“君子”與“紳士”的風度融合成一個禮儀之邦。在這部小說裏,校園內外,城市鄉野,皆正氣沛然。有那樣一群人,他們不僅同其國難家仇,也同其美醜善惡。可以說,“氣節”二字無時不體現出頂天立地的力量。
在我看到的這兩卷裏,融進了大量的中國古代美學意象,譬如梅園的描寫。有的花草名,就好像是《楚辭》中的香草異卉之名。這都是當代小說中罕見的。
深谷幽蘭,這是宗璞的境界,在寫作上於她是一個恰當的選擇。
我曾邀請她與一幹北大意昂來昆明。她當時固執地要下滇西,為的是完成《野葫蘆引》的第三卷《西征記》。我們都很擔心她的身體和眼睛,她卻是誌在搜集“遠征軍”的故事。
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會長沈克琦先生曾贈我一書:1944級西南聯大從軍同學所寫所編的《八百學子從軍記》。書打開來是地圖,當年聯大學子們從軍蹤跡幾乎遍布全國主要戰場。書裏回憶,一些人直接參戰,到環境險惡的緬甸蠻荒之地去;有的追隨孫立人將軍,有的還見到了馬歇爾;還有人參加了芷江受降,作了現場的紀錄。這本書的前言,讀來令人心酸。裏面說:“我們只想說,自己無愧於歷史,無愧於國人。”
宗璞寫《西征記》,專門用其中一卷來記載他們的功績,體現了她的史識。
近聞她的《北歸記》在《人民文學》雜誌上發表。驀然想起那年在馮鐘芸先生家裏,看見過一幅照片——在一部汽車上,有一群歡樂的人。馮鐘芸先生告訴我,這是她們準備要回北平了。旁邊一個小女孩,她說,那就是宗璞,十二歲。
而現在,宗璞先生在幾乎失明的狀態下終於完成這部小說。
馮家是名門望族,馮友蘭兄弟二人當年都在西南聯大。2009年我去臺灣采訪拍攝時,曾經在臺北與宗璞通過電話,告訴她我將去馮鐘豫先生家。宗璞說:“代我向六哥問好。”
宗璞的創作早年受過挫折,如今年事雖高,誌向卻依舊遠大。她要保存的不再是一顆紅豆,而是用病弱的手試圖保存這一頁巨大的史詩。
《未央歌》喚醒了“青春的中國心”
2009年秋天,臺北福華會館,西南聯大學人易君博先生拎了一大包資料來送給我,都是與西南聯大歷史相關的臺灣報刊資料與書籍。其中有一本鹿橋的小說《未央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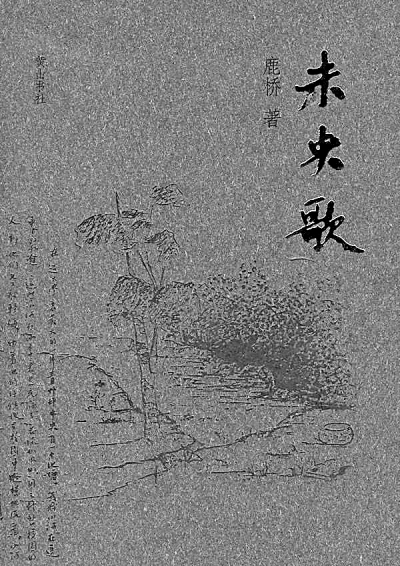
鹿橋的《未央歌》2008年首次在中國大陸出版
《未央歌》完成於1945年,直到1967年在臺灣由商務印書館發行,立即風靡一時,被稱為中國臺灣版的《青春之歌》。小說以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雲南和昆明的風光為背景,故事的主角是一群天真年輕的大學生,伍寶笙、余孟勤、藺燕梅、童孝賢……在烽火連天的歲月裏,在平靜純潔的象牙塔裏,他們彼此引為至友、畏友,有愛有怨、有笑有淚,並交織發展出一段屬於青春和校園的愛情故事。書中有關於友誼的描述、愛情的鋪陳,以及對校園精神的探討,表現了一代青年學子對真善美的追求與積極樂觀的生命態度。小說那些對於大學生群體的描寫與回憶,充滿十足的校園氣味,其青春氣息、青春語匯、青春審美、青春狂想,都是特有的,非親歷者不可編撰出。
贈我書的易君博是西南聯大政治系張奚若的學生,在臺灣“光復”時,老師推薦他上島參加接收,從此留在臺灣,可謂資深人士。據他說:“鹿橋,即吳訥孫,寫這部小說,那些人物都是有所指的。這些故事,以及小說裏的幾位人物,大家都知道的。他們幾個人都是西南聯大學生。一位是我們老師的兒子,他曾經做過國際貿易……他生活中有過一個女同學,他們的關系很特別。”
我一直覺得,《未央歌》中的學生生活有奢侈之嫌。書中寫他們經常收到家人寄來的罐頭,還有時髦衣服。其中主人翁所用所穿,與一般人的戰時生活相差很多。果然這部小說寫的是西南聯大的一個特定人群,出身上層社會的他們沒有饑寒之愁苦,而有《牡丹亭》裏的“遊園驚夢”氣息。他們在校園中是少數派,比之西南聯大的那些東北流亡青年、從華北淪陷區逃出的青年等,在生活的境遇和追求上,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也可以想見,在當時的西南聯大校園,確實存在著不同的風景、不同的人群生活。其兼容並包之氣量,像是一片大海。
《未央歌》還令臺灣讀者聯想到《紅樓夢》,一個原因是人物設置與愛情結局的類同。被視為“佳人”,多愁善感,一向被愛憐的女生藺燕梅,本來與“才子”余孟勤浪漫定情,卻又意外地情迷他人,自愧而遁入空門,成為修女,演繹了由“色”而“空”的哲理,帶有“人生如夢”的悟定。而一直站在旁邊的“姐姐”似的人物伍寶笙,則不動聲色地取而代之。伍寶笙是一個人際關系圓通的女生,尤其受教授夫人的青睞。最終,由教授夫人們將她與那位“人中之龍”的才子余孟勤撮合。夫人的背後站著教授。學生自然是要尊師的。這裏透露出一種“釵勝黛敗”的規則。
學者張惠在研究臺灣郵票的變遷時指出,臺灣對《紅樓夢》的趣味發生了“擁釵棄黛”的傾向。寶釵已經被看作是“現代性容貌身材、性格處事的一種追求”。《未央歌》的愛情結局與臺灣在《紅樓夢》人物上的取舍是一致的,此頗耐人尋味。
林黛玉是傳統美的產物,在今天的一些人看來“不適於現實的生存”,而遭到嫌棄。但我質疑,將文化詩意和理想之美與現實生存的本領相提並論,在邏輯上可以說得通嗎?在文化引導上,沒有庸俗化的嫌疑嗎?
據易君博講,吳訥孫寫這部小說的原因“是大多數人都覺得校園已經平淡消沉,不像抗戰的時期那樣,社會對知識分子是贊美的”。“他想把那個東西,校園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寫出來,就是說,希望回到抗戰時期的青年一樣,關心國事和時政,不要自私自閉,在校園裏面,應該關心國家的前途”。
《未央歌》給中國臺灣青年呈現了一個中國大陸“戰時校園”的文化氣氛和青春男女的精神風貌。在被日本帝國殖民統治51年後的臺灣,它喚醒了“青春的中國心”。這是這部小說最大的一個貢獻。
這本書在臺灣銷量很高,影響很大,它讓人們知道了西南聯大。
《未央歌》在寫戰時大學的環境方面異常真實。寫學生成群結隊一起逛大街,從文林街走到鳳翥街,看門聯,看過大年,吃米線,喝蓋碗茶。作者極其熟悉昆明的街巷市井,熟悉郊區的沙朗,他面對那些野外的風景產生了青春聯想。
書中,作者深深地沉湎於過去的學子生活中,流淌出大量的抒情文字。這是相隔海峽、遙望故土的情懷之作。其書名,與白居易《長恨歌》有關聯:“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故此部小說的感人至深處,不在“三角戀愛”,而是濃郁的思鄉之嘆。
攜帶個人的體溫
小說的確立,依靠一種精神價值。《圍城》旨在“哲思”;《南渡記》旨在“述誌”,講“氣節”;《未央歌》旨在“言情”。
同是“戰時大學”的親身閱歷,各有各的來路,各人所見所感觸的並不雷同。各人認為最重要的、必須表述的內容概不相類。這就是蘇軾說的“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意思吧。也許是我浸潤於史料太久的緣故,讀小說時常會有“隔靴搔癢”的不滿足感。“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每一部小說,也都不是歷史面貌的全部。
此外,西南聯大歷史,也不宜孤立起來看。它是沉浮於中國抗戰大史上的一葉扁舟。其中人物,來來往往,皆出入於那個時代的大潮中。這大潮至今沒有平息。它承載著先人與今人的體溫與靈魂之痛。
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古典小說一直有兩個傳統:一個是演義歷史,加以個人愛憎,可以稱之為“文以載道”的傳統。如《三國演義》之類。另一個則是“抒情”與“言誌”的傳統,如《紅樓夢》《浮生六記》之類。
在我看來,小說必須帶有個人“體溫和靈魂之痛”。小說的最高成就,不是“表現”,而是“感動”。小說的大美,在於以情感、性格、命運來激動人心。
最後我還想再提一部小說。
有一天我去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查閱《意昂簡訊》,看到一本海外意昂寄來的書。封面是彩色的畫,印著月與燈和一個少女。書名《月與燈依舊》。小說的語言有一種陳舊感,敘述則帶著一種感恩心。故事並不奇特,但如果把它與作者身世聯系起來,會感到這裏面有一種虔誠。
小說開頭寫一個舊時代的大家庭,老太爺與青春的女傭在傳統的格局裏有了孩子,大少爺認領了這個孩子,使她受到良好教育。但她一直覺得慈祥的老太爺與自己有一種特殊關系。這個女孩長大進入學校,隨之到了昆明,就是西南聯大。書裏面直接寫了蔣夢麟校長為意昂主持婚禮的情形。婚禮上,女生們穿上各種旗袍,在戰爭的大後方盡力維持自己的青春美麗。她們相互交流,怎麽做一條好看的旗袍。整個校園生活的主調是快樂明朗的。
抗戰結束,這個女孩以優異的成績得以出國深造。生活中出現了一位男士,時常在圖書館幫助她,並且不計較她的殘疾,向她求婚了。此後她們定居美國,生活幸福,擁有了一定的學術地位。
這本書中,除了蔣夢麟外,其余一看都是化名,作者的名字也是隱喻的。《月與燈依舊》很像是一部自傳體的小說,它表現出對戰時西南聯大生活的懷念。
這本小說印數很少,估計就只是在意昂之間流傳。這本單薄的小書,沒有技巧,沒有功利心,只是帶著一種體溫,隔洋飛來,落在意昂會的檔案中,更像是一封聯大意昂的家書,傳達著思念。
(作者:張曼菱,系作家、製片人,多年來致力於“國立西南聯大”歷史資源的搶救、整理與傳播工作)